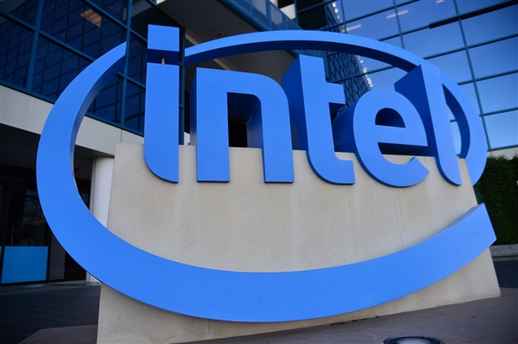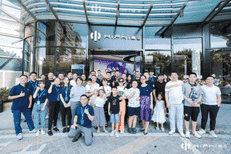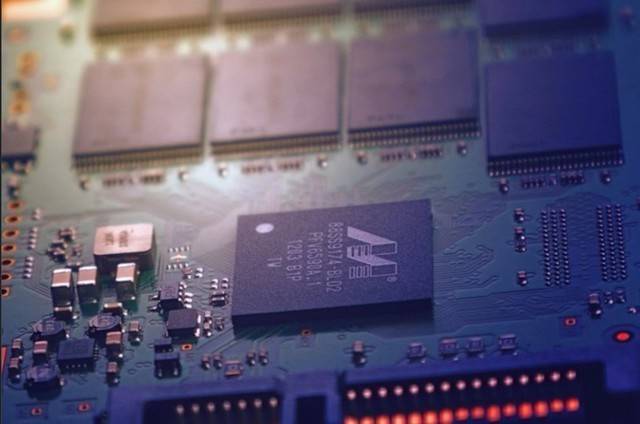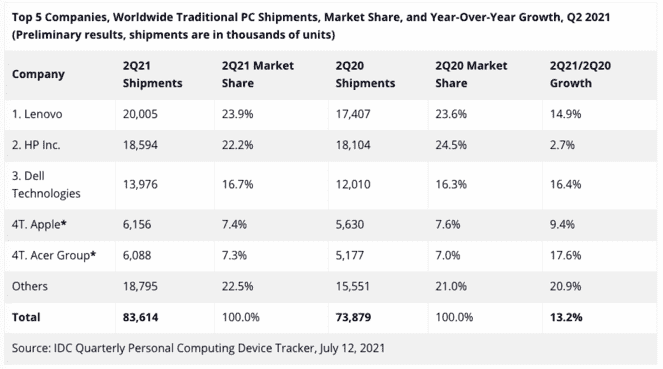做外婆家之后我发现:如果只为了钱 注定走不远
文/吴国平 外婆家创始人
我之前做过专业运动员,项目是田径中距离跑;后来做体育老师,在杭州上城区的一所学校;再后来我到杭州塑料工业公司做工人,我觉得自己体力好,做工人没问题。27岁那年,我把班组带成了市级劳动模范。
那时候结婚不用钱,生孩子家里补贴,房子是单位分的,父亲给的装修钱,他就一个愿望:我不能离开体制内,因为那是铁饭碗。
1996年单位分房子的时候我已经34岁,还向父亲拿钱,我觉得挺难为情。那年月我们工资都很低,养活一个家庭有困难,我们两天在我父母家吃饭,两天到丈母娘家吃饭。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要自理,就想着要赚点钱,改善生活。
当时国营企业的福利是,每年夏天发西瓜,过年发肉,所以工会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做了一个餐厅,想着增加员工福利。可这个餐厅做了一年就倒闭了,企业就在内部招标,想搞个人承包。
招标布告就贴在食堂里。我太太跟我说她想去做,我说这要跟老板说。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车间主任,大小也算个干部。我跟老板说我太太想做这个餐厅,他说:“也行。”
投标会在一个会议室里举行,我太太在前面参与投标,我穿着工作服站在后面看。我当时的心理价位是5万元,后来叫到7万元。我跑到老板那里说:“现在承包费这么高,我付不出。”老板说:“你举上去,付不出,到年底我给你签个字,你只要不亏钱就行。”我回去马上举到10万元,然后就中标了。
1998年,饭店开业,我是总指挥,我太太听我的,相当于现在的COO(首席运营官)。餐厅开出来十张方桌,两个圆桌,两个服务员。我太太什么活儿都做,招人、收银、服务、厨房打荷、买菜……
我带着两个服务员到现在的杭大路买了两条牛仔裤,两件汗衫就上场了。桌子是曲木材料,60块钱一张,椅子大概15块钱一把,加起来一套四人座的桌椅120块钱,一共花了两万块钱,我们的餐厅开业了。
当时的店名叫“外婆家家乡面”,是个面馆。我们没有过多思考店名,我是外婆带大的,结婚是在太太家这边办的,我儿子自然也是他外婆带大的,所以我对外婆特别有感情。这些东西没有特别策划,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
开业第一个月没赚钱,老婆说我卖得太便宜了,要涨价。我坚决不同意,我俩吵了一架。我开这家餐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希望给像我这样收入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消费场景,因为那时候的餐厅都很高大上,越贵越好,越大越好。
我们餐厅开业时,客单价是26元,外婆家现在3块钱的麻辣豆腐就是那时候出来的,那时候还有2块钱的拌面,2块钱的青菜,2块钱的啤酒。后来成本一直涨,价格就慢慢提高了,但现在也只有60块钱的人均。外婆家走的这条路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完全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那时候不知道要宣传。我们公司大概1800人,我跟工会说给每个员工送一张券,让同事都来吃,带人气。后面就开始一直排队,看到窗台上一排年轻人喝完的啤酒瓶,我开心死了。
2004年,我打算从国企出来,全职做外婆家。首先,经济层面上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其次,我觉得餐饮市场太大了,跟我之前做的药包材市场完全不一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间大、频次高,又是刚需,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产业。
要离开国企心里还是怕的,因为上一次我辞掉体育老师的工作时,回家被父亲骂了,而且1999年公司改制后,当时的我也算一个小股东。但做了外婆家之后我发现,如果只是为了钱,肯定是走不远的。现实问题解决之后,就得解决理想问题。
从体制内出来以后,回到家里,父亲还是念叨:“那么好的厂长不要做,去做个餐厅干嘛?”到现在,我一直做餐饮,我不想、也没能力做别的。虽然我也做民宿,但那是情怀的事情,更不是为了赚钱。
大概七八年前,去野马岭玩,我很喜欢那儿,就想能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看到黑瓦白墙就会有记忆。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杭一中旁,那时候还没有中河高架。那里有一条小小的河,两旁的房子跟现在的乌镇一样,院子里邻居之间都很融洽。后来住进商品房,邻居我一个都不认识。人文的东西越来越少,我想把小时候记忆里的东西留下来,也算是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弥补。
虽然我们更向往未来,但这种记忆不能瞬间就消失了。如果我能够把乡村留下来,让人们去回望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用我的话说就叫“留住记忆,留住符号”。
记忆是前辈留下的足迹,符号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我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创业也在杭州,对这个城市非常有感情。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总要留下点什么。留些东西在西湖边,是我的愿望。前辈给我们留下了楼外楼、知味观,外婆家能不能在西湖边留下来呢?这样一想,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多开100家店都有意思。